

老街不长,从东头到西头不过两千来米,只能算是一条小街,这条小街曾经是小城唯一的街,我儿时大多数的记忆都是关于这条街的。老街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解放路,为了纪念解放而得名,在叫做解放路之前它叫中山路,有了新的名字后原来的名字就让给了它身后那条和它一样老的小街。在它300年的历史中一定还叫过别的很多名字,这些名字一定也都有着时代的印记,如今又叫做“商业步行街”了,但我们习惯叫它老街,打我记事起,它就叫老街。
(一)
我成为老街的居民是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的1976年,老街上还明显留着上个时代的痕迹,一西一东相距不过千米的两座威严的大院分别挂着“利川县革命委员会”和“利川县革命委员会人民政府”的牌子。
那时,老街无疑是小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几乎县城里所有的党政机关都在两个大院里,全部的文化、教育、金融机构都聚集在这条街上,就连不多的几个商业机构,也零零散散的分布在这里,我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些凭票供应的商业机构,肉、糖、副食,什么都凭票供应,零散的几个小店也都挂着国营的牌子。

那时买盐、打酱油都是小孩的专利,大人们彼此问起孩子多大了,一句很常用也很经典的回答就是“能打酱油了”。隔着老旧的木质斜面柜台,踮着脚尖把盐罐或酱油瓶递进去。盐和酱油都是散装的,用一个极高极大的木桶装着,酱油桶上挂着几个大大小小的提子;盐桶上横着大秤,一头撮瓢一头秤砣。印象中,系着白围裙戴着白帽的营业员总能一次把盐称准,还总是不笑。
有时大人也叫我们去跑腿买一些别的东西,比如常用品火柴,一买就是10包,先是木梗的,后来变成了蜡梗的。买火柴可以集火花,象邮票一样,有一套单枚的,也有一套多枚的,三国演义、红楼梦的都有,还有风景,小时候集了很多,后来都不见了。还买“紫罗兰”牌洗发粉,倒进瓷缸里和水洗头,一包可洗短发两次,再奢侈就是“海鸥”牌洗发膏了。但这两样都属奢侈品,多数时候,用肥皂对付着就把头发洗了。

头发洗了自然干,长得太长时就得进理发店弄一下。老街上唯一的一家理发店离政府不远,是集体的。有电时,理发师傅用铁壳的电吹风把头发吹出型状来;没电时,用铁钳子加热了来弄干头发,看起来虽然恐怖,却从没出过危险。烫发也是用这种钳子,只是加热的时间长一些,烫出来的形状很像爆米花,俗称“包谷泡头”,追求时尚的男女常常是这种发型,不追求时尚的则是千篇一律短圆形的的“包包菜头”。圆形的理发椅子又高又大,转起来咯吱作响,我一坐上去就紧张,特别是推剪在脑后响起时。二十分钟下来,一个“包包菜头”就成型了,那时县城人出门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包包菜头”就是一个重要标志。

(二)
卖水是老街上的一道景观。七十年代初老街上才有了自来水,这之前用的水都来自城里的三口水井。最初自来水管只装进了单位,居民用自来水就在街上设了几处木屋,安排了几名孤寡老人卖水。早晚各开一次匣,一分钱一挑水。居民排着长长的队伍买水,队伍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水桶。除了早晚固定的时间,需要用水要么还到水井里去挑,要么在街上买——专门有人在不开闸的时候卖水,价钱涨到两分。
老街上还有卖茶的,多是老年人在自家门口摆个凳子,放几只玻璃杯,杯里盛些凉茶,盖一块玻璃挡灰。有空就在茶摊前守着,没空也不守。进城赶集的农民渴了站着喝上一杯,然后丢个一分的硬币在玻璃上,不给钱也没人讨要。如今大东门那棵歪脖子树下偶尔还有卖凉茶的摊子,玻璃杯换成了塑料饮料瓶,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盛着凉茶摆成一排,依旧无人看守,不知道茶价几何,也不知生意如何。

除了站着喝茶的凉茶摊,老街还有几处茶馆,供人坐着喝茶,也是老街居民一个休闲的去处。几张方桌、几条长凳、一碗盖碗茶,价格是三分钱一碗。到了晚上,茶价涨到五分,因为晚上有说书的,便多两分听钱。最有名的说书人是一个叫谢融的老艺人,评书说得好,特别是《江姐上船》那折,至今还有听过的人津津乐道。不知道评书什么时候没有了,也许是因为有了电影院,也许是因为谢融们没有传人。茶馆倒还是有几家,到了夜晚也还是人声鼎沸,打打小麻将,顺便也喝口茶。
(三)
严格地说老电影院并不在老街上,但它是老政府大院的一部分,大名叫政府礼堂电影院,也是老街的一部分。白墙、黑瓦、拱门,分外威严,拱门上有一颗红五星,至今还灰尘厚重地证明着它的年代。今年国庆,一位离乡三十余载的老人回利川来,在全然陌生的城里找寻往日的记忆,站在老电影院门前稀吁良久:三十载物是人非,只有这栋建筑让他依稀想起了旧日的利川城。如果再晚几年回来,也许连这点记忆也找不着了,它将成为超市、休闲广场还是商住小区——连它自己也无从得知。
这里曾是老街人打发闲暇时光最好的去处,在电视机还不曾普及的年代。遇到好的电影一票难求,倒卖电影票成了一个很来钱的职业。《少林寺》放映时是老电影院的鼎盛时期,几乎是万人空巷,全城的人携家带口兴高采烈地去看,在影院门口会发现无数熟悉的面孔,互相高声的打着招呼。凡放映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全城的学校都组织学生去看,中学生小学生,排着队鱼贯入场。我很怕看这种电影,看一场电影就要写一篇作文,因为那时课外活动的确不多。

所幸还有一种东西是不需要买票,也不需要写作文的,还能学到很多知识,那就是有线广播。中学时我每天上学要走半条街,广播是我最好的朋友,早上踏着《东方红》的旋律走在天刚发白的老街上,听“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午去上学就听“午间半小时”。有一天早晨上学时看到一个进城卖柴的,刚把柴担放在电杆下准备歇一会,广播正巧就响了。卖柴人惊慌失措,挑起柴就跑,口里还直嚷嚷“我可没碰它啊!”
最初广播和电话共用着一条线,县广播电台每天有一两个小时的自办节目,节目结束时,播音员会叮嘱:“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请把开关倒向电话一边”。由于和电话共用线路传输,听完广播要把开关倒回电话那端,否则就打不了电话。

打电话让人怀念至今,因为在夜里伸手不见五指也可以准确的打电话,更不用记电话号码。电话上没有拨盘、也没有按键,一个黑乎乎的话机,握住摇把猛摇几转,拿起来就有总机小姐接转,多方便啊。如今移动电话“爱打,随便打”了,摇把电话是在哪一年悄然退场的呢?
(四)
炸爆米花是关于老街的“声、色、香、味”俱全的回忆。家门口就有一个炸爆米花的点,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常常从家里撮几捧米或包谷就欢天喜地飞也似地向教育局大门口跑去。那时爆米花是小孩的主要零食和家庭里待客的主打品牌,所以总是排起老长老长的队。只消把自家的篮子或盆排在别人后面,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在附近玩耍,一锅爆米花两斤,时间是固定的,瞅着前面有多少个人,就可以估计着时间玩上多久再来。

爆米花的家什很简单,一个煤炉、一桶拌得湿湿的煤、一个风箱,外加一个有着气压计和圆摇把的大肚子的铁家伙,拖着一条长长的看不清颜色的尼龙口袋,口袋下方开一口子可以倒出爆好的玉米花。我最害怕也最期待爆米花成型时那惊天动地的响声,看戴着草帽黑着脸和手的师傅有节奏地拉风箱,摇动摇把,间或移开爆花机加两小铲煤,渐渐地速度慢下来了,就知道快爆了。捂着耳跑一边看师傅起身将爆花机塞进尼龙口袋上方的橡皮大口上,麻利地踩一脚机关--“砰”地一声巨响,雪白或黄白相间的米花、玉米花便喷入尼龙口袋,香气四溢,半条街的人都能闻到。付上两三毛钱加工费,两斤米或玉米就变成一大口袋爆米花提回家去,扎紧袋口,可以放上大半个月,每天上学时偷偷抓一大把揣荷包里,整个上学路上都是快乐的。
除了爆米花,上学路上还有许多可以吃的东西,桂花糕是其中最让我难忘的。做桂花糕的老师傅姓程,就住在小学对门那条窄小的巷子深处,巷子里住了几家人,都姓程。老程师傅有一手祖传的做桂花糕和醪糟汤圆的手艺,我无数次眼巴巴地望着老师傅的端着一大蒸笼桂花糕的身影从巷子深处出来,一路飘着桂花糕浓郁的甜香。椭圆的、黄澄澄、胖乎乎的桂花糕五分钱一个,端出来就被一抢而光。而老程师傅从不多做,三五笼卖完成了,就只专心卖他的醪糟汤圆。醪糟甜而纯正、汤圆洁白细腻,巷子里挨着墙放着几条矮长凳,吃的人多,挤挤满满的坐满了一巷子。

桂花糕后来没有了,因为老程师傅没有了,手艺没有传下来。而醪糟汤圆的手艺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也是家家户户的日常食品,也就传了下来。巷子寂寞许久后,又挂出了“老程家喜妹子”的招牌,几条长凳又加了矮茶几。卖的还是醪糟汤圆,味道也还是老程家的,但我只是路过,望望,我想念桂花糕。
(五)
图书馆是我关于书最早的记忆。过了羊岔街往东走就是图书馆、文化馆和川剧团,走过文化馆前的几个花坛就是川剧团。经过川剧团长长的围墙,就到了图书馆。看书的时候偶尔会从川剧团飘来几缕琴声和吊嗓声,不过现在早不叫川剧团了,叫过民族艺术团,也叫过山茶艺术团,院子很老旧了,人才倒出得不少。
那时常常去图书馆是因为和我住在同一个大院里,在图书馆工作的亚萍姐姐,我常常去借书看,同时也看亚萍姐姐上班的样子。她脸上总是带着温婉恬淡的笑容,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神采。每次去图书馆,亚萍姐姐总会会从密密麻麻的书架上找出一堆书给我--按规定每次只能借两本书,还书时再换两本。我看书的速度快,囫囵吞枣,一目十行,不到一个星期就抱着一堆书去换下一堆书。很快,图书馆不多的少儿读物便被我看遍了,就到学校对门的茂槐书店去。

那时茂槐书店的刘老板还在,跛着一条腿出入在店里,一张没有笑容的脸。他儿子极聪明,起初跟我同班,没几天竟跳级到上两个年级去了,我常到茂槐书店转悠,想找到刘同学跳级的原因。看了不少茂槐书店的书,也没能跳成级,相反因为严重偏科,十年寒窗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只是保留了读书的习惯。从学校毕业还没踏入社会那段时间,没钱买书,突然发现了新大陆:老检察院旁边有一家书店,收旧书也卖旧书。我便从家里偷了书去卖。我卖过《莎士比亚全集》,却记不得买了什么书,依稀记得老板是个内向的年轻人,戴着黑边的眼镜。
再后来又发现老街背后的中山路上有个“古今书社”,可以租书看,五毛一本,多看一天加一毛,很合理。店主老袁佝偻着腰背,戴着老花镜在挤挤满满的小屋粘贴一些破损的书页。每周还出一期贴报,贴的《南方周末》。贴在硬纸板上,挂在老司法局大门不远的墙上。我看书的速度依然很快,有一段时间常去还书、租书,去得多了,老袁就不再收我的押金。找书时总能看到和老袁一样老的老伴在另一间小屋里做缝补衣服、编簸箕之类的零活,也许靠租书不能养活两个老人吧,我想。

再后来就很少借书、买书和租书了,接送孩子上幼儿园时路过中山路,不见了老袁和他的古今书社,不见了他的贴报栏。老街上也不见了茂槐书店,不见了我曾经卖过书的那家书店,只有图书馆还在。文化馆到艺术团之间的花坛变成了一排服装店。图书馆安静的呆在艺术团老旧围墙后的角落里,图书馆里,还有我温婉恬淡的亚萍姐姐。
(六)
我从小长大的院子在老街正中的教育局。从大门进去穿过篮球场时,我总要打量一下球场四周的青石栏杆,小时候每天在这里玩,就觉得这青石的栏杆和别的地方不大一样。石栏杆一头刻着头尾相交的双蛇太极八卦图,球场四面都有石阶供人上下,石阶旁边随意散落着几个石凳模样的东西--最近我才知道那叫“柱础”,木头做的大柱子不直接触地,不会潮湿腐烂。
但柱子还是不见了,中国和欧洲的古建筑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多用木结构,欧洲多用石结构,石头是不朽的,可以用来记录历史;而木质的结构无论多精美绝伦,保存下来的都不多。柱础上当年一定有威严的梁柱,石栏杆一定护卫着一座雄伟的大殿,但如今柱础和石栏杆都孤独的沉默着:同治四年的县治图上,这个院子是文庙。

从文庙往东过羊岔街到大东门之间还有几座大院,分别是同治年间的张爷庙、戎捕署、城隍庙和武庙,没有文庙那么幸运保留它原有的功能。有的在土改后分给了老百姓,有的奖励给了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利川籍烈士的亲属,看起来就象一个大杂院,高高的石门槛后,一个公共的堂屋,一个青石板的天井,十几家人围着天井住着,堂屋走的人多了,脚底带的泥便形成了“千脚泥”,那些高低不平的圆圆的小土包有时会在夕阳下映出一点光来,但多数时候是暗淡的。
我喜欢看那几个院子,想走进那高高的石门槛,想象自己也住在那些院子里。院子里有忙忙碌碌的生活,院子门口摆着很多小摊,补鞋的、卖菜的、烧肉的、卖杂货的,我最喜欢的是卖鸭血汤的,五分钱一碗,每次去看外公,外公总是从中医院出来走几步路到旁边的大院子门口买一碗给我,外公是有名的中医,他一脸慈爱,看着我贪婪的吃完,告诉我说:鸭血清热。

我慈祥的外公没有了,再也没有人买鸭血汤给我吃,但倘若外公还在,鸭血汤却没有了,连同那几座大院子。旧城改造时,老街上的私房得以很优惠的政策进行翻修,几乎在商业步行街竣工的同时,很多木质结构的私房变成了砖混结构、瓷砖的脸面,一条新的街形成了,那几处大院是公有的,新修成了商住楼,成了老街新的标志性建筑。
我很遗憾没有留下那几座大院的图片,但我始终能想起高高的门槛前叫卖的吆喝声。赶集的日子,老街上还是熙熙攘攘,人声鼎沸,补鞋的、卖菜的、烧肉的小摊都还在,这就是老街,这就是县城的生活形态。

你见过这样的利川老街吗?
你对老街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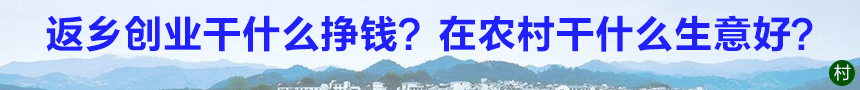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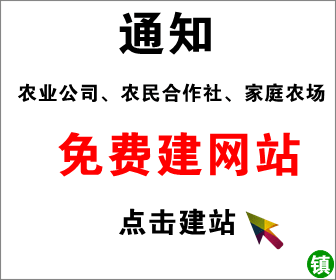
 苏ICP备18063654号-3
苏ICP备18063654号-3 苏公网安备 32011202000276号
苏公网安备 32011202000276号

